- 相關推薦
硝煙中的迷失(上)——抗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話語
抗戰之前的知識分子話語雖然已經面對著國家權力話語和民間大眾話語的雙重擠壓,卻仍然在艱難地發展著,特別是那些優秀的創作,都比較多地繼承著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話語的基本精神。抗戰爆發之后,知識分子話語更進一步陷入困境,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沉重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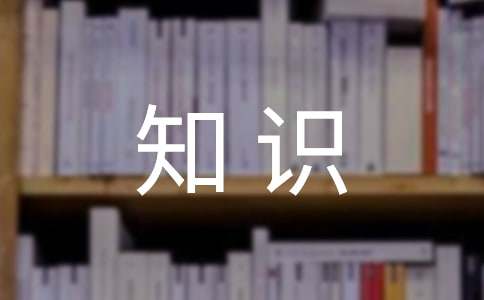
一、民族主義旗幟下的集結與陷落考察當時文壇實際,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抗戰文學是在民族主義旗幟下集結的。
自從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許多學人都用啟蒙與救亡這兩個概念來談論20世紀中國文學。然而,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展并不僅僅是李澤厚所論述的啟蒙與救亡的二重變奏,而是由啟蒙、救亡和翻身所構成的三重主題變奏。由于歷史的境遇,中國新文學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同時并存著三種意識:人的意識、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三種意識分別產生了三個中心主題:啟蒙、救亡、翻身。五四新文學以人的意識為主導,形成了啟蒙主義文學主潮,雖然在整個五四時期三種意識基本能夠和諧統一而沒有表現出激烈的沖突,卻已經隱含了各種矛盾。雖然三種意識和三種話語并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系,但是,知識分子話語更關心人的解放,民間話語更看重階級的翻身,而國家權威話語無論什么時候都更青睞于民族意識和與之密切相關的愛國主義。國家權威話語與民族意識的聯系并不奇怪,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國家就是統治機器,而且只有國家權力更有條件宣稱自身代表全民族的利益。30年代初期的中國文壇非常清楚地分出了幾個陣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以民族意識為中心,主旨在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鞏固,更多地體現了國家權威話語的意愿。左翼文藝運動以階級意識為中心,旨在階級的翻身解放,更多地體現了民間大眾話語。這兩種力量尖銳地對立著,但就其文化性質來說二者之間大同小異。過去的研究由于視角的問題而過分夸大了二者之間的對立性,忽略了它們之間鮮明的共同性質和產生這共同性的同一文化價值基礎。事實上,民族主義文學和左翼文學在文學觀念、審美意識和對文學的具體要求等方面,都表現著高度的一致性。他們都否定五四新文學以人的解放為中心的啟蒙主義,都反對個性主義而張揚群體意識。不同只在于前者所張揚的群體是民族,而后者所張揚的群體是階級。在抗戰之前,雖然雙方都向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精神發出挑戰,但并未能夠真正動搖文學主流發展的方向。雙方都把文藝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創作的園地里卻成果稀少,真正顯示著創作成就的是這兩大陣營之外的作家和那些雖在集團之中而未被集團吞沒的堅強個體。
事實上,文學在抗戰前夕已經向民族主義靠攏。左聯的解散就是一個明顯的標志。“兩個口號”的論爭雖然進行得非常激烈,但雙方都提出了新文學必須為民族的解放與獨立而斗爭的目標和任務。它顯示著30年代以階級意識為主體意識的左翼文學向民族意識的歸順。周揚主張“國防文學”,目的就是要求“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1)雖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仍然保存了“大眾”的字樣,意味著仍然存在階級意識,但是,卻也承認在新的形勢下文學必然地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里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求”。(2)人們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文學不能不接受統一戰線的號召,要求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作家到統一戰線的陣營里來,以便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一切力量,以爭取民族的自由與解放。“統一戰線”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但無論怎樣解釋,都無法抹殺一個事實:統一戰線并不是烏合之眾,它必然統一于某種權威。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形成的統一戰線必然服從于民族權威,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結成的統一戰線必然要強化國家權力。強調民族中心意識意味著強調民族團結,而團結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團結在國家權力周圍。從根本上講,這是民間話語中的政治因素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知識分子話語的獨立精神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這種矛盾卻沒有表現出來。甚至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那些昨日權威話語的激烈反對者對國家權威的順從。“國防文學”的口號就是一個鮮明的標志。
抗戰開始,意識形態和審美傾向上存在的矛盾都開始轉入次要地位,一切服從抗戰的要求。各派作家聯合起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其《簡章》中明確地宣布著他們的宗旨:“以聯合全國文藝家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完成中國民族自由解放,建設中國民族革命的文藝。”在《告全世界的文藝家書》中,他們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是中國人,當此祖國阽危,全民族遭逢空前浩劫的時候,我們知道什么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是中國的文藝人,我們熟知我們歷史上偉大的天才每一次臨到民族對外作戰以求生存的時候,是怎樣做的,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所在!”當時的情形確如郭沫若在《抗戰與文化問題》中所說:“'八。一三'以來,所有國內的種種頡頏狀態幾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于抗戰的力量也漸漸地集中了起來,就已感覺著有集中的必要。就簡單拿文化問題來說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盤歐化的那些空洞的論爭,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著鼓舞的,是抗戰言論,抗戰詩歌,抗戰音樂,抗戰戲劇,抗戰漫畫,抗戰電影,抗戰木刻……”左翼作家也不再把蘇聯放在自己祖國之上,更不再高唱“無祖國”之論。文學全力配合抗戰,民族意識成為文學的中心意識。文學集結于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終于取得全面勝利。
無論我們如何理解這種選擇。文學在民族主義旗幟下的集結給文學帶來的結果是不容忽視的。從理論上講,我們完全可以證明偉大的戰爭應該產生偉大的文學,但歷史提供給我們的現實卻不能不承認:置身于偉大的戰爭中的作家卻沒有產生出偉大的抗戰文學。抗戰初期的創作主要是報告、特寫、通訊、墻頭詩、街頭劇等小型作品。盡管從當時到現在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有人論述那些作品的偉大之處,但文學藝術水平的降低卻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化,大同小異的作品形成了“抗戰八股”的不良景觀。那些作品告訴我們,文學為抗戰付出了代價。值得思考的是,戰爭對文學的影響不應該是負面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學史告訴我們,戰爭不是導致文學水平低落的原因。半個世紀之后回顧這個時期的文學,我以為,文學水平之所以降低,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學在強化民族意識的同時出現了內容和形式雙重的失落:一方面是陷入國家權力話語的重圍而失落著真實的主體;另一方面是俯就大眾而降低了藝術水平。雙重失落的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未能完成自身人格的現代性轉化,一旦置身于某種潮流之中,就容易失掉自我。創作上普遍的水平降落啟示著后來者:即使作家有真摯的感情,一旦拋棄了自己的話語立場和話語形式,就很難寫出成功的藝術佳作。
從當時的創作實際考察,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作家們不再有自己思想和認識的獨特性。這僅僅是因為戰爭嗎?戰爭并不導致作家思想的消失。在戰爭中,知識分子當然要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而吶喊,但它應該仍然是獨立的個體
的吶喊,是帶有自己獨特個性色彩的思想和情感表達。然而,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作家們一旦服務于戰爭,卻立即失掉了自己的聲音,放棄知識分子的話語立場而完全淹沒于國家權威話語之中。
這是一個值得充分注意的歷史現象。它說明著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意識的欠缺。其實,這種欠缺在此之前早已暴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大批經歷過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禮的作家已經轉變方向,背離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建立的知識分子話語立場而走向了不同的群體。他們缺少強大的自我和堅強的個性,雖然追隨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潮流,但畢竟不象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那樣具有堅實的根基,新潮浸染了他們衣衫的花斑卻未能使他們生長出獨立地支撐自己頭顱的筋骨。所以,一旦大潮退去,他們必然立即到某個群體中去尋找依靠。無論普羅文學運動,還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都否定五四新文學,都反對個性主義而強調集體意識。其中表現的正是一些沒有完成現代轉化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弱點。他們希望自身有所依附,希望集團作戰,并且希望有人為自己作主或者指揮自己的行動。這種弱點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更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不再要求創作自由,不再強調人格獨立,而且主動要求組織的管理和紀律的約束。一些文學史著都曾經指出這一事實:“從各地集中到武漢的作家,一致感到缺乏嚴密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以致影響到文藝工作者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甚至文藝宣傳、創作和出版往往形成自流,因此迫切要求文藝界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3)如果與五四先驅相比,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狀態嗎?然而,這種描述是準確的,從《抗戰文藝論集》保留的材料就可以看到,以群在抗戰開始寫的《關于抗戰文藝活動》中認為當時的文藝活動有兩項急迫的任務,其中之一就是文藝應該象軍隊一樣有“健全的組織”,他說:“全國的軍隊必須有統一的編制,統一的指揮,然后才能做到配備恰當,進退有序的地步,文藝作家也同樣,必須自身有整齊嚴密的組織,然后才能有系統,有計劃地執行自己的工作。”(4)半個世紀之后,讀著這樣的文章,我們可以設想,讓文學家也象軍隊一樣按照計劃執行自己的寫作任務,能夠創作出什么樣的作品呢?這種主張竟然由處于邊緣的知識分子自己提出,更充分地說明著知識分子對自己話語立場的徹底放棄和在民族主義旗幟下的自我迷失。
一些人不僅自己放棄創作自由和精神獨立,而且要求他人也統統照此辦理,以達到步調一致。有兩件事值得在此提及,一是所謂“與抗戰無關論”引起的風波;一是所謂“反對作家從政論”導致的批判。其實,梁實秋并非主張文學與抗戰無關,他的原話是“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5)結果卻引起發了激烈的批判。反對者從根本上否認在抗戰中有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好象寫作或者發表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就是對抗戰的破壞,好多梁實秋成了反對文學服務于抗戰的漢奸。沈從文這個自稱“鄉下人”的作家在這個特殊的歲月卻恰恰表現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他在1939年發表文章《一般與特殊》,對一些作家投筆從政提出批評。因為在他看來,作家從政之后滿足于一般宣傳,是創作質量下降的原因。他并不反對文學創作為抗戰服務,卻實在看不起一些文人滿足于風云際會,以文化人的身份去獲得一官半職而得意洋洋。沈從文的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評。由此可見,當時的文壇已經容不得不同的聲音。
經過歷史的風雨,這些舊賬已經越來越清楚。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積極維護民族主義中心意識的卻不是老牌的御用文人,而是剛剛被招安的叛逆。他們接受了國家權威話語,并且用這權威話語要求不愿意完全放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立場的作家。這種批判雖然是舊日積怨在起著作用,但總讓人想起梁山好漢們一旦有朝廷之勢可仗,那威風便今非昔比。昨天自己處于江湖,與異己的爭吵也只能是村野的叫罵。今日既然進入廟堂,便可指責一切異己者不忠不孝。
回顧20世紀中國文壇,可以發現一個規律,無論哪一個階段,做出貢獻的往往是默默無聞埋頭苦干的作家;那些總是活躍在文學運動浪尖上的人雖然以制造風波引人注目,但其作用卻往往是建設性極小而破壞性極大。他們往往反叛也激烈,投降也容易,今天是叛逆,明天就成了教訓叛逆的打手。他們常常反權威,但只要從權威那里獲得認可,就會立即匍匐在地山呼萬歲。他們常常領導新潮流,并且用鞭子驅趕不愿追隨者,但正是這種行為一次次導致了知識分子話語及其承載的現代性的失落。
二、大眾化傳喚中的沉沒文學既然要全面地服務于抗戰,就要首先致力于喚起千百萬民眾的抗戰熱情。要喚起民眾抗戰的熱情,就必須適應宣傳對象的要求。于是,如何使文藝創作被大眾所喜聞樂見成為文學的當務之急。在形式上,要為大眾喜聞樂見,就不能不考慮舊形式的利用。因此,如何利用民族舊形式就成了一個實踐中急需解決的問題。由此引起的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是20世紀文學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它在理論上沒有什么建樹,但產生的影響是重要的,甚至改變了20世紀文學的發展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在聽命于權威話語而服務于抗戰的過程中沒有完全喪失自身,是由此而來的舊形式的利用和大眾化使文學走向了徹底喪失自身的道路。知識分子話語在與權威話語的矛盾和斗爭中沒有完全失落,但在遷就和迎合民間話語的過程中卻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沼澤。
抗戰一開始,文壇就響起了大眾化的呼聲。來自文壇內外的力量都紛紛呼吁文學走向民間,走向大眾,實現大眾化。我們知道,文藝大眾化問題不是抗戰開始后才提出來的,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作家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大眾化的討論中,魯迅曾經發表過很好的意見――他擔心文藝會因此而俯就大眾,會成為“大眾的幫閑”。抗戰開始之后,這個問題重新提出并引起人們的重視是必然的。正如茅盾所說:“本來文藝大眾化運動應當和國語運動聯系起來的。但是目前我們講大眾化,卻不能拘泥于這個理論。我們現在十萬火急地需要文藝來做發動民眾的武器,我們不能等待到大眾學會藍青官話那一天。”(6)“因為在全面抗戰的今日,我們的作品如果還是只能達到最少數的知識青年群中,就是文藝這武器尚未充分發揮它的力量!”(7)
為了宣傳而要求文藝通俗易懂以便能夠被廣大民眾所接受,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可非議的。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民族處于危急的關頭而文學不在某種程度上發生變化。也無法想象作家們會完全拒絕以通俗的形式為戰爭服務。但是,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委員長或者他的宣傳部對文藝提出的戰時要求,而是一些文人對文學提出的主張。一些人甚至認為:“在抽象的理論上,非大眾的抗戰文藝是不能存在的。抗戰的文藝同時必然是大眾的文藝。”(8)“現在,面對著這樣緊張的局勢,我們應該嚴重地提出:'大眾化'是一切文藝工作的總原則,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都必須沿著'大眾化'底路線進行,在文藝工作底范圍內,應該沒有非大眾化的文藝工作,更
沒有反大眾化的文藝工作”。(9)
要求文學全面大眾化,舊形式的利用產生的后果已經不必細說。民間舊形式的基礎上產生不出現代的文學作品,它導致的必然是文學藝術水平的嚴重退步。這種退步在宣傳性的作品中不可避免,任何人都不應該對其苛求,但為宣傳而粗制濫造卻不應該成為藝術的標準。文學應該努力向著高水平發展,不應該放棄對藝術水平和深度的追求。然而,一些很有影響的人物卻干脆主張徹底放棄文學的藝術水平要求,徹底放棄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單純以服務于抗戰宣傳為標準,甚至直接反對對藝術水平和理論深度的追求。郭沫若在《抗戰與文化問題》中說:“抗戰所必須的是大眾動員,在動員大眾上用不著有好高深的理論,用不著有好卓越的藝術——否,理論愈高深,藝術愈卓越,反而愈和大眾絕緣,而減弱抗戰的動力。”周揚在《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中也說:“我們現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這種大眾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當前息息變化的實際情況,而不是離開實際,關起門來去創造什么'偉大的作品'.”雖然這時候的郭沫若已經是第三廳的廳長,與權威話語的合流使他不再是一般的知識分子,正如他在1926年穿著國民革命軍的軍裝向青年發出做革命文學家的號召一樣,本身已經不是知識分子? 納?簟H歡??捎謁?納矸荼暇共煌?謖諾婪?裙?竦徹僭保?湎??饔檬歉?饗緣摹?/P>
民族形式的討論涉及的不僅僅是形式問題。文學要為大眾所喜聞樂見,決不僅僅是形式問題的解決所能夠達到的。要實現大眾喜聞樂見的目標,就必然要迎合大眾的價值觀念、文化心理和審美習慣。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必然導致文學現代性的喪失。在20世紀中國,文學大眾化的要求與現代性的目標是格格不入的。原因很簡單,由于中國的現代化是被動的,作為一種被動的現代化,其動因不是本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長而是外來文化的沖擊,而最先接受外來文化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民間大眾。所以,現代性主要由知識分子話語承載而不是存在于民間文化之中。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現代性沒有在民間大眾中扎根生長。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話語與民間大眾話語在文化性質上有著本質的差別。前者是外來的,后者是本土的;前者是現代的,后者是傳統的。五四新文化之所以新,就新在它以西方思想武器反傳統,新在它的非本土的現代性質。因此,要求民族化,就不能不意味著對知識分子話語的否定,就不能不意味著對現代性的否定和對傳統性的弘揚,也就不能不意味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精神的背離。民族化和大眾化是相互聯系的,民族化必然導致大眾化,大眾化也必然帶來民族化,兩者都可以導致傳統的復歸,也必然導致五四知識分子話語精神核心的顛覆。
【硝煙中的迷失(上——抗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話語】相關文章:
硝煙中的迷失(下)——抗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知識分子話語08-06
當前文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研究08-17
關于《祝福》中的新舊兩代知識分子08-17
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文學性的問題探源論文08-07
生活中激勵自己的話語07-22
中青班學員在結業典禮上的發言05-19
讀中積累、讀中感悟、讀中遷移《雨點》08-15
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話語權08-06
在反思中成長 在成長中反思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