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權利質權制度的困惑與出路
【內容提要】傳統民法將權利質權定位為與動產質權相并列的一類質權是引起該制度在當今司法實 踐中陷入種種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我國制定民法典之際,應當將權利質權從傳統民法理 論的窠臼中解脫出來,將其與權利抵押權相并列,形成一種體系協調的權利擔保制度, 這是解決以上困難的上策。【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權利質權/權利抵押權/占有移轉
權利質權制度,是以所有權、不動產用益權以外的可轉讓的財產權為標的的質權。自 羅馬法以降,權利質權制度一直是作為與動產質權相并列的一類質權規定在大陸法系和 英美法系國家的私法制度之中。然而近年來,隨著大量無形財產的產生,可用以出質的 財產權種類空前繁多,使得傳統的權利質權理論捉襟見肘。那么,在我國制定民法典物 權編之際,我們是繼續沿襲傳統民法的模式將之納入質權體系,還是對其另起爐灶而予 以創新,這將是各位學者和政府所不得不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為此,筆者不揣淺陋, 將對此予以探索,以求教于諸位同仁。
一、難言的困惑——權利質權制度的尷尬
傳統的民法理論總是信奉這樣一個教條:權利質權制度是一項通過權利的占有移轉來 進行擔保的制度。例如,史尚寬先生認為:“權利質權依債權證券之交付、質權設定之 通知或其他方法,使發生占有之移轉或其類似之效力。”(注:參見史尚寬:《物權法 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頁,第417頁,第388頁。)依此理論,在以 可讓與的財產權擔保時,必須先移轉該財產權的占有。那么,如何移轉財產權的占有呢 ?傳統民法首先引進了“準占有”的概念——“以自己所為的意思而行使財產權就視為 對該財產權的準占有。”(注:參見[日]田山輝明:《物權法》,陸慶勝譯,法律出版 社2001年版,第151頁。)在此基礎上,有學者創造性地提出了權利占有移轉的概念,即 當財產權由一方的控制之下轉入另一方的控制之下之時應當認為發生了權利的占有移轉 。(注:參見陳小君、曹詩權:《質權的若干問題及其適用》,《法商研究》1996年第5 期。)據此,學者們提出了各種形形色色的財產權占有移轉方式。在債權質權場合,債 權證書的交付意味著債權的占有移轉。如《日本民法典》第363條規定,以債權為質權 標的的,如有債權證書時,質權的設定,因證書的交付而發生效力。在證券質權場合, 權利質權的交付以證券的交付、質權設定之通知或其他方法而發生占有移轉的效力。( 注:參見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論文選輯》(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 第865頁。)而在知識產權質權場合,質押合同在國家相應主管機關的登記常常被作為質 權生效的條件,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第L.132—L.134條規定,軟件使用權的質押合 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并應登記在國家工業產權局特別設置的注冊簿上。至于股權質權 ,其表現更是形態多樣。在無記名股票場合,其質權的設定通常是以股票的交付作為占 有移轉的條件;而在記名股票及其他股權設質場合,則通常以股票或股權的登記為財產 權占有移轉的條件。正是這些不同的占有移轉形態,導致了權利質權理論在解釋上的危 機。權利質權理論所遇到的第一個困惑來自于司法實踐。法官們突然發現,以債權證書 的交付作為債權質權移轉占有的規則難以自圓其說。按照傳統民法的解釋,債權證書的 移轉代表債權占有的移轉,但是,如果當事人沒有債權證書或者債權證書丟失了但有其 他證據表明該債權的效力,那么此時的債權質權是否有效呢?對此,我國臺灣地區已有 的所謂“判例”指出,無債權證書的債權在出質時,無須交付證書,立法上仍承認其效 力(1985臺上1212)。這是因為,債權證書是用以證明債權存在的文件,它僅有證明債權 存在的效力,與債權本身是形式與實質的關系,債權證書的滅失,并不必然表明債權本 身的滅失。照此推斷,在債權質權設定之時,即使無債權證書的交付仍然能夠成立債權 質權,此時不存在債權占有的移轉問題,也就意味著以債權證書的移轉作為債權占有移 轉的做法并不合乎邏輯。
權利質權理論所遇到的第二個困惑來自于知識產權質權理論上的爭議。在知識產權領 域,學者們對知識產權質權的設定是否需要交付證書的問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例如, 史尚寬先生認為,專利權證書與債權證書不同,債權證書表示債權的存在,而專利權證 書并非表示權利,理論上不應以證書的交付或移轉占有等要物行為為必要。因此,德國 專利法第6條認為專利權出質為不要式之行為。(注:參見史尚寬:《物權法論》,中國 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頁,第417頁,第388頁。)對此,多數學者表示贊同, 認為知識產權權利證書并非為流通證券,出質人向質權人交付知識產權證書,并無多少 意義。(注:參見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頁。)當 然,也有學者認為,為了防止出質人在設定質押后擅自轉讓知識產權,應當要求出質人 向質權人交付知識產權證書,如商標注冊證、專利證書等。(注:參見王利明:《物權 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70頁;策yuè@①:《專利權質押中質權 人的利益保障》,《知識產權》1988年第3期。)實際上這些解釋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 為專利權證書是國家頒布的用以表明權利存在的一種證書,在證明功能上與債權證書并 無二致,交付專利權證書與交付債權證書具有類似的功能。它的交付會對專利權人行使 專利權造成一定的障礙,但它在遺失后同樣可以補辦,因此是否交付專利權證書對質權 的存在的確影響不大。所以,如果認為證書的移轉就代表財產權的占有移轉,不免牽強 附會。特別是在以著作權中財產權出質的場合,著作權人并無可供質押的權利證書,當 然無交付的可能。另外,商標權在出質后,出質人即商標權人負有保全該權利的義務, 仍應繼續在商品或服務上使用其注冊商標,否則將在一定期限后被撤銷該注冊商標,而 商標注冊證的持有又是行使該權利的必要條件,所以商標權即使在出質后也只能由商標 權人持有權利證書。因此,以證書的交付作為財產權移轉占有的表征并不恰當。
權利質權制度所遇到的第三個困惑來自于登記移轉理論。在發現有些權利質權不能通 過證書的交付來達到占有移轉的目的后,一些立法例又將登記作為占有移轉的表征。例 如,《法國商法典》第91條第3款規定,以在公司注冊簿上過戶方式進行轉讓的金融、 工業、商業或民事公司的記名股份、受益股和公司債,以及國家債權人名冊上登記的記 名債權,也可作為擔保通過在上述的注冊簿上過戶方式設定質押。此外,在知識產權質 權問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將知識產權質權的設質登記作為質權的生效要件。那么, 上述這些設質登記是否必然意味著財產權的占有移轉,或者說該財產權的行使權由出質 人移轉至質權人手中了呢?顯然不是,因為設質登記僅僅是表明該財產權已處于出質狀 態,出質人不能對它隨意處分,而不意味著出質人已將該權利交由質權人行使或對其進 行自由支配,質權人對這些權利的控制力極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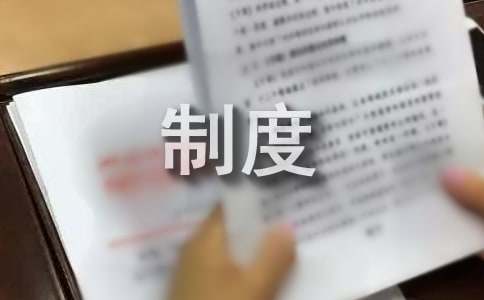
,當然不能解釋說該財產權已經移轉 占有。
權利質權制度所遇到的第四個困惑來自于與權利抵押權的關系協調問題。通說認為, 權利抵押權是以所有權以外不動產物權或準物權為標的的抵押權,如以地上權、永佃權 等權利為對象的抵押權。羅馬法及近現代一些國家的民事立法均確立了權利抵押權制度 。例如,德國《地上權條例》第11條、第12條規定,地上權可以獨立地作為抵押權的標 的。在土地上有建筑時,建筑應該隨同地上權抵押。《日本民法典》第369條第2款也明 確肯定地上權及永佃權也可為抵押權的標的,準用不動產抵押的規定。顯然,權利抵押 權和權利質權的共同點表現在二者均以可轉讓的財產權利為標的,只不過權利抵押權的 標的僅為不動產的用益物權而權利質權的標的相對廣泛得多而已,債權、證券上的權利 、知識產權等權利均可作為權利質權的標的。那么,僅根據用以擔保的標的的不同而將 其區分開來是否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呢?如果從上述擔保權的設定來看,這種區分的意義 已日趨淡薄。一是因為類似動產的權利與類似不動產的權利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人們很 難對一些財產權做出準確的劃分。按照傳統民法的理論,有形財產可劃分為動產和不動 產,設定于有形財產之上的權利可根據其附屬財產的性質而劃分為動產和不動產,即附 屬于動產上的權利通常被認為具有動產性質,附屬于不動產之上的權利被認為具有不動 產性質,(注:參見《法國民法典》第516—536條。)例如有價證券上的權利被認為是動 產權利,而土地上的用益權被認為是不動產權利。但在現代社會,做出這種區分日益困 難,一些權利如知識產權、股權很難說它們是屬于動產上的權利還是屬于不動產上的權 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7條規定: “以公路橋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動產收益權出質的,按照擔保法第75條第(4 )項的規定處理。”也即,不動產的收益權如公路橋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等收費權 可以作為擔保法第75條第(4)項所規定的“依法可以質押的其他權利”來質押。結果是 這一做法遭到了不少批評,因為按照傳統民法的理論,不動產收益權上設定的擔保似乎 應作為權利抵押權來對待。二是因為權利質權在設定方面已越來越接近于權利抵押權, 二者之間出現了交融局面。例如,在目前各國所設立的權利質權制度中,多數權利質權 在設定之時需要通過登記方式進行公示,這與權利抵押權的設定幾乎一致,難怪有些學 者明確指出,權利質權雖名為質權,但其擔保的作用反近于抵押權,謂之介于一般質權 與抵押權之中間領域,亦無不可。(注:參見史尚寬:《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 版社2000年版,第388頁,第417頁,第388頁。)在這種背景下,人為地根據標的的差異 來區分權利質權與權利抵押權,難免會讓立法者和司法者感到棘手和困惑。
二、難解的疙瘩——導致困惑的原因
美國著名學者博登海默先生曾經指出,法律的基本作用乃在于使人類為數眾多、種類 紛繁、各不相同的行為與關系達致某種合理程度的秩序,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就需要設 計一些有助于對社會生活中多種多樣的現象與事件進行分類的專門觀念及概念。然而, “一個概念的中心也許是清楚的和明確的,但當我們離開該中心時它就趨于變得模糊不 清了,而這正是一個概念的性質所在。”(注:[美]E·博登海默:《法律學、法律哲學 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頁。)正是由于人們對 權利質權概念和性質認識上的模糊,才使這一制度在當今面臨著種種困境。因此,要解 開這一疙瘩,必須從該制度的本質著手。
盡管早在古羅馬時期就已存在以地上權、用益權、債權、居住權等權利為標的的權利質 權,但有關權利質權性質的爭論卻一直是民法上的一個喋喋不休的話題。在日本,從191 2年到1989年期間,權利質究竟是否是物權的問題曾經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甚至連大學者 都為此爭得面紅耳赤。(注:參見[日]石田喜久夫:《口述物權法》,成文堂1982年版, 第496頁。)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有關權利質權的性質曾存在兩種主要學說:一為權利讓 與說,該說認為質權的標的應為有體物,權利之上不得再生質權,所謂的權利質權不過 是以擔保為目的而為的權利讓與;二為權利標的說,該說認為權利質與物上質并無本質 上的差異,所不同者,僅是標的而矣,也即,物上質是以物為其標的,而權利質是以權 利為其標的。(注:參見倪江表:《民法物權論》,臺灣正中書局1965年版,第352頁。) 在目前的理論界,權利標的說已成為通說,整個權利質權的體系莫不以之為基礎而建立 。從積極的角度來講,權利標的說承認財產權可作為擔保的對象,這對于發揮財產權的 經濟效用十分有價值。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一些立法者正是因為過分強調權利質權與動 產質權的近似性,而忽視了權利質權制度自身的特點,最終使它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換言之,權利質權與動產質權標的上的近似性并不等于說權利質權在具體規則上就一定 要沿襲動產質權的相應規范。
在厘清了上述問題之后,我們不難發現權利質權制度的癥結所在,即人們在設計權利 質權制度之時均以動產質權的相應規范作為權利質權制度的范例。例如,《德國民法典 》第1273條第2款規定:“關于權利質權,除第1274條至第1296條另有其他規定外,準 用關于動產質權的規定。”《瑞士民法典》第899條第2款、《日本民法典》第362條第2 款、《意大利民法典》第2807條及我國臺灣地區所謂的“民法”第901條亦有類似之規 定。所謂“準用”,系指該制度與動產質在立法上有相同的理由為避免立法上的重復而 類推適用動產質權的相應規范。但是,“準用”一詞的使用,也有其內在缺陷,如使法 律的適用趨于復雜,在法律的解釋上易生歧義,等等。(注: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頁。)正是因為確立了類推適用動產質權的思 想,所以立法者想當然地將動產質權的規范套用于權利質權制度之上。例如,動產質權 在設定時需要移轉出質的動產,所以立法者就要求權利質權在設定時也要移轉占有。而 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出質的財產權具有無形性的特點,不可能通過物理方法移轉占有, 所以立法者又想當然地設計出以權利證書或權利憑證來代替移轉的方式,如移交債權證 書、有價證券等等。當發現上述做法在實踐中難以通行之時,立法者又構建了通過登記 移轉占有的方式,其結果是造成了與權利抵押權制度的重合。
導致權利質權制度步入困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傳統民法有關財產權利性質的分類 。按照傳統民法的觀點,依附于動產上的財產權屬于動產范疇,其制度規范比照動產制 度設計;依附于不動產上的財產權屬于不動產范疇,其制度規范比照不動產制度設計。 這種分類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按照古羅馬學者的分類,物可分為有體物和無體物,有 體物包括各種有外在形體的財產,
而無體物包括地上權、地役權、債權等各種財產權。 盡管有體物與無體物同屬財產,但其在法律適用上卻相差甚遠,如無體物不可能像有體 物那樣通過物理方式予以占有、使用和處分,特別是知識產權這種無體物產生之后,其 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上的特殊性常常使傳統民法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所以,對無 體物(即財產權)在利用時,不論是進行何種方式的利用,均應考慮其特殊性,而不應機 械照搬有形財產的法律適用規范。因此,將財產權利比照其依附的客體而分為類似動產 的權利與類似不動產的權利的做法本身就存在內在缺陷,特別是就知識產權而言,將其 歸位到何種財產權都是不適當的。
三、艱難的抉擇——權利質權制度的出路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使法律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并使社會秩序規范 化和協調化,為此,定位準確、規范明晰的法律模式就成為現代立法者所追求的法律價 值之一。當我們在發現權利質權制度在當今社會所陷入的種種困境時,究竟是繼續墨守 成規而在未來的民法典中將其作為與動產質權相并列的一類質權,還是對其大膽創新而 構筑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新的立法體例呢?
筆者認為,法律的活力在于創新,惟有對傳統的不適應現代法律發展的觀念予以更新 ,才能使這一古老的制度煥發新的活力。具體而言,首先,我們應當毫不吝惜地拋棄那 種將財產權利分為類似動產的權利與類似不動產的權利的做法,而應當根據各類財產權 的特點分別構建適合其個性的法律適用規范。其次,我們可以拋棄“權利質權”的傳統 歸類(即不再將其列入質權體系之中),將其與“權利抵押權”合并,并稱為“權利擔保 ”制度,形成一種與動產擔保、不動產擔保相并列的一類擔保制度。采取上述模式的合 理性在于:第一,放棄“權利質權”的傳統歸類,可以在理論上和立法上擯棄那種機械 照搬動產質權的做法,可以更好地張揚該制度的個性特點,便于人們認識該制度的特殊 性。第二,將“權利質權”制度與“權利抵押權”制度合并,能夠形成一種完整的權利 擔保制度,便于立法體系上的協調。這種擔保制度的特點在于以財產權為擔保的對象, 在擔保制度的設定和實行時充分考慮用以擔保的財產權的特殊性而分門別類地設計其特 殊的法律適用制度,從而形成與有形財產擔保迥異的法律制度。第三,構建以“權利質 權”和“權利抵押權”為核心的權利擔保制度,能夠解決權利質權制度所遇到的種種困 惑。傳統民法所設計的占有移轉模式或登記模式,其實質無非是解決擔保的公示性問題 ,將設質登記解釋為財產權的占有移轉無疑是自尋煩惱。所以,在未來的權利擔保模式 下,一切可讓與的財產權均可作為擔保的客體,我們可以根據各種財產權擔保的需要而 設計出不同的公示模式來維護交易的安全,而不必去考慮其是否意味著權利的占有移轉 。例如,有價證券在擔保時,由于它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權利,持有有價證券就可以在一 定條件下直接行使該權利,因此有價證券擔保時必須交付憑證而不必進行擔保登記。至 于知識產權擔保、債權擔保、土地使用權擔保、有限公司的股權等權利擔保,無法通過 移轉占有方式來公示,因此應以登記方式來公示。所以,采取這一模式的好處就在于能 夠合理地針對各種財產權設定恰當的公示方法,而不必將一種僵化的占有移轉模式硬套 在各種權利擔保之上。對于一些性質上難以厘清的財產權如公路收費權上的擔保,人們 也不必挖空心思去論證其屬于權利質權抑或權利抵押權,而可直接以登記作為擔保設定 的公示方法,從而有利于法律體系的協調。
總而言之,解決現存權利質權所遇到的種種困惑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登記制度、 提存制度以及財產評估制度的完善,同樣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厘清權利質權制度 與動產質權制度、權利抵押權制度之間的關系,并設計出適合未來發展的立法模式,將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選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王右月
【權利質權制度的困惑與出路】相關文章:
漁業權是漁民的固有權利08-06
動產質權設定合同03-04
自然資源權利物權化的思考與立法建議08-05
論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權利屬性08-05
權利即是權利作文08-05
水仙的困惑08-17
育兒困惑08-25
困惑的作文05-18
民法中的水權制度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