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檢討
債務人的一般財產是其債務的總擔保,如果債務人不當減少該一般財產,勢必給其全體債權人造成損害,使債權人債權有不能實現的危險,為資救濟,債的保全制度應運而生。在我國法學理論中,代位權制度似乎被當然地作為債的保全的形式之一而為學者津津樂道——至少在筆者所見到的有關債的保全的論述中大多如此。然而,正如經驗告訴我們的,在一些看似公理式的結論中往往存在著許多似是而非的東西,因而,在許多情況下,對一些基本命題的追問可能是必要的。在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中,……前言
一、傳統民法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歷史沿革
依通說,代位權制度發端于法國民法典,羅馬法上尚無此制。《法國民法典》第1166條規定:“但債權人得行使其債務人的一切權利和訴權,惟權利和訴權專屬于債務人個人者,不在此限。”(注:《拿破侖法典》,李浩培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55頁。)關于法國民法創設代位權制度的立法考量,有學者指出:“蓋法國民事訴訟法并無如德國民事訴訟法,設有債權人得依強制執行程序,對于其債務人之債權予以強制執行之規定,故有在民法中設債權人代位制度之必要。”(注:馬維麟:《民法債編注釋書》(三),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5(1996)年版,第1頁;同說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62頁。)在法國民法典制定當時,法國適用的是1667年法國民事訴訟王令。關于1667年法國民事訴訟王令的內容我們無局可考,但是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從1667年民事訴訟王令中照搬過來的”,(注:張衛平、陳剛編著:《法國民事訴訟法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而法國民事訴訟法除金錢債權外,沒有債權人得對于債務人之債權予以強制執行之規定,(注:張衛平、陳剛,前引書,第311頁以下;《法國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羅結珍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49頁以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測1667年民事訴訟王令亦確無此制。上述觀點,結論上可資贊同。
1896年制定的德國民法典對債的保全包括代位權制度均無規定,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德國,債權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享有的權利無任何權利。與法國法不同,德國法另辟蹊徑,在1877年制定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設有較為完備的規定。(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謝懷@①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310頁。以下關于德國民事訴訟法的條文,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該譯本。)關于該規定的具體內容,容后詳述,于此不贅。
1898年開始施行的日本民法典和1929年公布、現仍在臺灣地區生效的“中華民國民法”均從法國立法例,就債權人代位權制度設有明文,(注:參見《日本民法典》(王書江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條;“中華民國民法”第242、243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自民事訴訟法中獨立出來的日本民事執行法和1940年公布、現仍在臺灣地區生效的“民國強制執行法”對債務人的債權及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亦均有詳細之規定。(注:《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白綠鉉編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頁以下(以下關于日本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該譯本);“民國強制執行法”,第115-122條。)因而,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就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及其他財產權所享有的權利問題,實行的是代位權與強制執行并存的二元制立法體例。
通過代位權制度的比較法考察,我們看到,代位權制度并非大陸法系各國所共通的制度,因而,該制度并無必然的合理性。而且,該制度的始作俑者法國所以有此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沿革上的理由而非體系上的考慮,因而該制度在邏輯上和價值上是否妥適,仍有很大的檢討空間。
二、傳統民法債權人代位權構成要件之檢討
(一)傳統民法債權人代位權的構成要件
在傳統民法下,債權人代位權,因其所代位行使權利內容的不同,可分為請求行為之代位與保存行為之代位,而在請求行為之代位,又根據債權人債權種類的不同,分為種類債權之代位權與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代位權,因其種類的不同,構成要件有所不同,分述如下,以作為后文討論的基礎:
種類債權之代位權是指債權人享有的債權為種類債權而發生的代位權。其構成要件包括如下三項:(1)須債務人已陷于無資力,不能清償其到期債權;(2)須債務人怠于行使其權利;(3)須債務已屆清償期或陷于遲延。在法、日民法主張以債務已屆清償期為已足,在日本民法履行期屆至前尚得主張裁判上之代位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則以債務人陷于遲延為必要。
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是指債權人享有的債權為特定物債權情況下而發生的代位權,該種代位權系由日本、我國臺灣學說、判例發展而來。其構成要件包括前述須債務人怠于行使其權利和須債務屆期(或遲延)兩項,而前述債務人須陷于無資力要件則無之。
保存行為之代位,是指為防止債務人權利之變更或消滅,所為的保全債務人權利的行為。如債權人為防止債務人對第三人債權的訴訟時效期間經過,代債務人請求第三人給付從而中斷訴訟時效。在保存行為之代位,其要件包括須債務人已陷于無資力和須債務人怠于行使其權利,而須債務人已屆期(或遲延)則無之。
(二)種類債權代位權之檢討
1.須債務人已陷于無資力要件
如果債務人尚有資力清償其債權,即使其有不當減少財產的行為,這也只屬于債務人權利處分自由范圍內的事情,不會對債權人的債權實現產生任何影響。在此情形下,即無置債務人處分自由和第三人對債的相對性的信賴利益于不顧,而賦予債權人代位權的必要。只有在債務人已陷于無資力,其不當減少財產的行為才會危及到債權的實現,此時,根據利益權衡,才應賦予債權人代位權。因此,該要件的設計對于代位權的制度價值而言是絕對必要的。
2.須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要件
如果我們認為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會導致其財產價值的消極減少,則該種行為就可能危及債權實現。那么,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是否會導致債務人財產的減少呢?
本文認為,在這里首先應注意財產價值的主觀性,債務人財產的價值對債務人和債權人而言是有所不同的。自債務人角度言:其若積極行使權利,或者使享有的權利性質發生變化,效力增強(在債務人對第三人享有的權利為債權的場合),或者使權利恢復圓滿狀態(在債務人對第三人享有物權的情形),無論如何,較之行使前在質上均有所增加;而如果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則享有的債權仍只能為債權,物權亦不能恢復圓滿狀態,從而應增加的財產沒有增加,財產價值消極減少。
但是,從代位權的制度價值來看,其立足點在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因而該制度所關注的應為就債權人而言的財產價值。而債務人的財產對于債權人而言的價值,是否會因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而減少,在不同立法例,情況則會有所不同:
在法國法,若債務人積極行使權利,權利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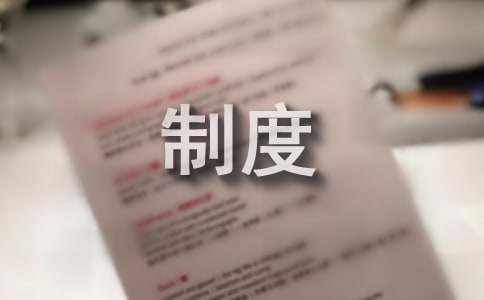
的物為債務人所有,債權人對之得聲請強制執行;但若其不行使,標的物仍為第三人所有,債權人即不得對該標的物直接為強制執行(因為其與第三人間并無基礎法律關系存在),而且,如前所述,在法國法上,債權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也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從而該標的物對債權人的債權實現而言,沒有任何價值。兩相比較,顯然其怠于行使行為使就債權人而言的財產價值消極減少。從而在法國,該要件的設計尚屬必要。
在德國法,若債務人積極行使權利,債權人的利益狀態與法國法相比并無不同;但若其怠于行使,則此時該行為并不會導致債務人權利的消滅和效力的減損,該權利仍然存在(當然,如果該種怠于行使行為導致訴訟時效期間的經過,其權利效力會大打折扣,但這是保存行為之代位問題,與此處所論種類債權之代位權無涉),而且,也不會改變權利的歸屬,該權利仍然屬于債務人。因而,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關于債權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強制執行的規定,債權人在將來亦得將債務人權利的標的物(或者該標的物的變形物,如因履行不能債務人權利轉化為損害賠償債權的情形)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就此而論,債務人是否積極行使權利,對債權人的債權實現而言并無不同,因而在德國法上,即無肯認債權人代位權的必要。
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在其民法典制定之時,代位權制度或有其存在之理由。(注:如民國強制執行法制定于1940年,在1929年制定民法典時尚無對債務人債權及其他權利得為強制執行的立法。)但至少在其民事訴訟法或強制執行法就對債務人對第三人的債權或其他財產權得為強制執行有所規范后,當事人間的利益狀態即與前述德國法相同,因而代位權制度已無存在之余地。也正因為此,有學者指出:“我國民法(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筆者注)……亦有對債權人代位權‘重復規定’之嫌。”(注:馬維麟,前引書,第1頁。)不惟如此,這種重復規定,還會徒增理論上的困擾:“日本學者之間,就先有代位訴訟后,再就同一權利提起收取訴訟(注:收取訴訟,發生于強制執行程序中,其詳后述。)之情形,有無抵觸重復起訴之問題,見解頗不一致。……原因在日本民法一面引進法國民法固有之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他面于強制執行程序采用德國法之收取訴訟制度,從而兩種制度未經調整而發生問題。”(注:陳榮宗:《強制執行法》,三民書局印行,1989年12月版,第578頁。關于該種立法,日本學者也有激烈批評,“如日本民事訴訟法權威學者三個月章教授(應系指三■月章教授——筆者注)即曾譏嘲該國民法第423條之立法為‘屋上建屋’,甚至以‘畸形妖怪’、‘不當代替物’、‘實體法學者不理解及漠視程序法之紀念碑’等諷之。”見戴世瑛:“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目的、發展、存廢與立法評議”,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十七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第106頁。)
在該要件的檢討中,我們會發現立法史上一個饒有興趣的現象:在法國法和德國法,無論其規定代位權制度還是強制執行制度,它們均與整個法律體系相協調。但到了日本法和我國臺灣法,則出現了如前所述的不協調,其原因在于:在日本法,其民事執行法效法德國民事訴訟法,其民法典卻較多地受到了法國民法典的影響,而德國法與法國法的某些規定是異質的、不能兼容的;在轉道日本效法德國的中華民國民法,日本法的某些規定則未經充分消化即依樣畫葫蘆地照搬了過來。這一沿革提醒我們,任何制度均有其特定的生存環境,我們在借鑒先進立法的時候也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不能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3.須債務已屆清償期或陷于遲延要件
在“須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要件的檢討中,我們已經指出,在德、日及臺灣地區,種類債權之代位權已無肯認之必要,故該要件之檢討,僅于法國法有其意義。
本文認為,對于該要件的檢討,首先應該明確的一點是:債的保全制度旨在維持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從而保障債權人債權的實現,而對債權人而言,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僅于強制執行時始有其現實意義,因而債權人所關注的,應為在強制執行時債務人的責任財產是否減少。其次,我們應當注意代位權制度下債務人行為的性質:在代位權制度下,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在性質上為消極的、持續性的不作為,在權利得行使之時對債務人未行使權利,并不必然導致債務人責任財產的減少。因為自該時點至聲請強制執行期間,債務人仍有積極行使權利,而使該權利標的物作為執行標的的可能性。因而,只有在聲請強制執行時,債務人的怠于行使行為是否會導致責任財產的減少方可確定。
因而,從邏輯角度言,只有在強制執行程序啟動后,債權人始得行使代位權。規定“須于債權屆期或遲延”,似嫌過早。但若規定須于聲請強制執行時始得行使代位權,則此種代位權與對債權的強制執行又有何異?
而且,將債權人得行使代位權的時點提前至債權屆期或遲延,使債權人在其與債務人間法律關系未經裁判確定的情況下即介入債務人事務,還可能在代位訴訟中產生一系列難以甚至無法解決的難題。
問題首先在于:債務人能否參加代位訴訟?如果能,其訴訟地位又應如何?如果債務人能參加訴訟,則其或站在債權人一方,或站在第三人一方,或與債權人及債務人均處于完全對立之地位。就債務人與第三人權利問題,債務人與債權人利害一致,而與第三人利害相反,但若就債權人代位資格問題為觀察,(注:關于該問題,有學者認其為代位訴訟標的之一(陳榮宗:“債權人代位訴訟與既判力范圍”,載氏著《舉證責任分配與民事程序法》,“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1984年2月再版,第184頁),有學者主張其僅為原告起訴的地位而已(陳榮宗等:“代位訴訟既判力研究”,載《民事訴訟法之研討(二)》,三民書局,1987年9月版,第22頁楊建華先生、第30頁陳石獅先生、第38頁王甲乙先生之發言),惟無論如何,債權人代位資格為當事人爭執之事由,則學者普遍認同。)因為代位權的主張系以債權人對債務人有權利存在、債務人已陷于遲延及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之事實為基礎,所以債務人與債權人系處于對立之地位,而與第三人利害一致。因此,債務人與債權人和第三人均既有利益一致之處,又有利益相反的地方。因此,債務人若參加債權人與第三人間的代位訴訟,其訴訟地位問題無法安排,故其應不得參加訴訟。
但如果債務人不能參加代位訴訟,則在債權人、債務人、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平衡方面便會產生諸多問題:其一,代位訴訟判決的既判力應否及于債務人?其二,在代位訴訟進行中,債務人得否對第三人另行起訴?其三,債權人提起代位訴訟后,債務人對其權利得否再為處分?其四,如果在代位訴訟中,法院認債務人已陷于遲延,而在就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法律關系的訴訟中,法院又作出相反判決,此時二者矛盾應如何協調?
為解決上述難題,學者可謂絞盡腦汁,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注:關于該問題的討論,詳可參見陳榮宗,前引書;陳榮宗等,前引文。)但這些方案均在某些方面不能盡如人意。那么,在苦思冥想仍難有解決之道后,我們是否也應該反思一下代位權制度本身?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不是訴訟法上先建立了理論,才有債權人之代位訴訟,而是先有了債權人之代位訴訟,然后訴訟學者就已既成的制度,來探討如何在訴訟理論上,使其周延。但是正因為本身就是一個先于理論而存在的東西,沒有辦法擺得很好
,因此各說事實上,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而已。”(注:陳榮宗等,前引文,第26頁范光群先生之發言。)本文以為,上述諸問題的出現,正是債權人代位權使債權人過早介入債務人事務造成的。
4.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債務屆期后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的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就債權實現而言的債務人責任財產的減少,因而在種類債權應無肯認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必要。
(三)特定物債權代位權之檢討
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并不以債務人陷于無資力為構成要件。在種類債權之代位權中,我們已經指出,無資力要件對于實現代位權的制度價值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已經偏離了代位權的制度價值。很多學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認其系為實現特定債權,而非維持責任財產,(注:邱聰智:《民法債編通則》,輔仁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1987年版,第314頁;史尚寬,前引書,第462頁。)因而與代位權制度價值已大相徑庭。實際上,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所以會出現,只是為了防止代位權的規定成為具文——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這種采取雙軌制的立法中,代位權制度在種類債權中極少適用,而恰恰也是在那里,關于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的理論特別發達。也就是說,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只是為發揮代位權制度之規范功能而設,在立法論上,無為此專設規定之必要。而且,承認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也難以避免上述代位訴訟中所面臨的難題。
(四)保存行為之代位
保存行為,如中斷訴訟時效的行為,第三人破產時申報債權的行為。此等行為,如果債務人怠于行使,可能會使其權利效力減損,甚至使該權利無從實現。比如,債務人怠于行使權利致訴訟時效期間經過,第三人又以時效抗辯的,債務人的債權即無從得到滿足。此時,債權人既不得對債權標的物為強制執行,而且對債務人債權聲請強制執行也無意義(第三人仍得主張對債務人的抗辯),因而如果債務人并已陷于無資力,則必然會危及債權人的債權實現,在此種情形下,肯認債權人代位權應為順理成章。
三、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替代(注:如前文所述,保存行為之代位,有獨立存在之價值,且其不涉及強制執行問題,故本部分論述,不包括該種代位權。)
上文分別從歷史沿革與構成要件的角度對債權人代位權制度進行了檢討,本部分將力圖從制度價值的層面對該制度進行考察。
在代位權制度中,為保障債權人債權實現的利益,一方面限制了債務人的處分自由,另一方面使第三人尚須對債權人代位權的資格問題進行攻擊防御,無疑增加了其額外負擔。但是,債務人濫用權利在先,而第三人對債務人的抗辯也并不因代位權的行使而受影響,對第三人的利益尚不構成根本性的妨害,“兩害相權取其輕”,賦予債權人代位權在價值判斷上尚無可厚非。
但是,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債務人的權利處分自由和第三人對債的相對性的信賴利益,因而應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制度。如能有一種妥善的替代制度,該制度即無存在之必要。本文認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即為一種比較理想的替代制度。
(一)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概述
債務人對第三人所享有的權利,只要具有財產價值,即為債務人財產之一種,以之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具有邏輯之可能性。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德、日及臺灣地區均有規定。
1877年制定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就對債務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設有較為完備的規定。該法第八編“強制執行”,首先根據執行債權種類的不同,分為“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和“關于物之交付與作為不作為的強制執行”;在“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又根據執行標的的不同分為幾種,“對債權及其他財產權的強制執行”即為其中之一,而對“債權的強制執行”又分為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對動產請求權的強制執行和對不動產請求權的強制執行;在“關于物之交付與作為不作為的強制執行”中,對“第三人保管的物的交付”(該法第886條)也有所規范。日本及臺灣地區效法德國,對該問題的規定與德國大同小異。
可以說,在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覆蓋范圍方面,德國的強制執行制度與法國民法的代位權制度大體相當,因而,二者存在替代之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就其他標的的強制執行不同,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會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和行為,因而,該制度能否既不妨害第三人權利,同時又能實現對執行債權人、債務人的公平保護,仍需考察。若能,則其為一種妥善制度,自然可替代債權人代位權制度;若否,則尚需比較其與代位權制度,然后從中選擇一種危害較小的制度。
下面本文即結合比較法的有關規定,對強制執行各程序當事人的利益狀態進行剖析。
(二)對強制執行程序中當事人利益狀態的考察
債權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依執行債權種類的不同,可分為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和關于物之交付請求權的強制執行。物之交付請求權的強制執行與對金錢債權強制執行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在后者,若執行標的為動產或不動產,須由法院拍賣或變賣標的物;在前者,則可不經此程序而徑將標的物交與債權人。而這一點,對于各方當事人利益尚無影響。因而,此程序中當事人的利益關系,與對金錢債權的強制執行并無不同,本文放在一起考察。
就執行程序而言,對債務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扣押命令階段和換價程序階段。
1.扣押命令階段
扣押命令,民國時期“強制執行法”稱為禁止命令。關于扣押命令,《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29條第1款規定:“法院應扣押金錢債權時,應禁止第三債務人向債務人為支付。法院應同時向債務人發出命令,不得對債權為任何處分,特別不得收取債權。”
在該階段,對債權人而言,如果債務人債權并不存在或者其上有抗辯,而第三人又未對此提出異議,則將可能使債權人在不能就該債權獲得執行利益的同時,也因而錯過就債務人其他財產強制執行的機會。為防此弊,德國法系各國均課第三人以說明義務,若違反該義務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損害,第三人應負賠償之責。(注:參見《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40條第1款,《日本民事執行法》第147條。)應該說,該種規定,對債權人利益保護堪稱周到,對第三人也難謂過苛。
對第三人而言,扣押命令生效后,其不得向債務人清償,此時如果債務已屆期,依民法原理,第三人可將標的物提存以從債務關系中解脫出來,(注:《日本民事執行法》第156條第1款對此亦有明定。)對其利益亦無影響。
2.換價命令程序
在換價程序,其執行方法計有四種,即移轉命令、收取命令、支付轉給命令以及難以收取的債權的換價。
移轉命令,日本法稱為轉付命令,是指執行法院所發的將債務人對第三人的金錢債權移轉給執行債權人的命令。移轉命令生效后,在執行債權人、執行債務人和第三人之間發生民法上債權讓與的效力,債權人的債權視為清償,執行程序終結。收取命令,是指執行法院所發的授予執行債權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的金錢債權直接收取的命令。支付轉給命令,是指執行法院所發的,就債務人對第三人的金錢債權,命
第三債務人向執行法院支付,再由執行法院轉給債權人的命令。
應該說,移轉命令借助于民法中債權讓與的法律技術,大大簡化了執行程序,而且,與民法中債權讓與一樣,第三人的利益并不因此而受影響。對債權人來說,雖然移轉命令生效后該債權不能清償的危險也歸由債權人負擔,但是這是債權人自己選擇的結果,自然應當承擔選擇的風險;而一個理性的債權人,也只有在第三人資力充足的情況下,才會選擇進入該程序。故該程序不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
在收取命令和支付轉給命令,如果第三人沒有異議,自覺履行對債務人的債務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第三人對債務本身有異議,則此時即應賦予債權人提起收取訴訟的權利。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款規定:“債權人對于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于收受前項通知后十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并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學者稱此種訴訟為收取訴訟。(注:德國法對于收取訴訟無特別規定,但由于在德國,債權被扣押后,債權人即取得扣押質權(《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04條),而依德國民法典,質權人應有權向第三債務人請求包括提起訴訟。)這樣,通過賦予債權人收取訴訟權,使債權人得以干預債務人的事務,因而該種權利為程序法中規定的實體權利。收取訴訟權使債權人權利可以得到充分保護,但這是否會對其他當事人的權利構成不應有的妨害呢?
收取訴訟由于是債權人代債務人的地位,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訴訟(這一點與代位訴訟同),因而發生債務人應否受該判決結果拘束,亦即收取訴訟判決既判力范圍問題。在該問題上,雖然學者之間觀點分歧,(注:學者論爭,其詳可參見陳榮宗,前引書,第571頁以下。)但本文認為,使該判決的既判力及于債務人,在法理上與當事人利益衡量上應均可成立。這是因為:首先,在收取訴訟中,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法律關系已經裁判確定,無爭執之余地,而在對第三人的關系方面,雙方利害關系一致,均在于謀求第三人之清償;其次,在比較法上,多規定在收取訴訟中,債權人對債務人有訴訟告知的義務(《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41條、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款);再次,在收取訴訟中,債務人得以訴訟參加人的地位參加訴訟。(注:如臺灣地區“民事執行法”第58條第1款規定:“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系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于該訴訟系屬中,得為參加。”)因而,其實體權利不致在未經其參加訴訟的情況下即為裁判確定;最后,如果由于債權人的過失導致敗訴,債權人對債務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42條、《日本民事執行法》第158條)。這樣,債務人既有事前保障,又有事后補救,對其保護,可謂周到。而且,判決既判力既然及于債務人,則第三人可免兩次受訴之苦,對其利益,亦無妨害。
如果扣押的債權是附條件或附期限的債權,或因有對待給付或因其他原因而難于收取時,應如何處理?德國法規定得較為簡略,只規定“法院依申請可以不命轉付而命令以其他方式進行換價”(《德國民事訴訟法》第844條第1款);臺灣地區“強制執行法”規定“得依聲請,準用對于動產執行之規定拍賣或變賣之”(該法第115條第3款);《日本民事執行法》則規定執行法院可以根據債權人的申請,發出以執行法院所決定的價額,向扣押債權人以讓渡代替其收取而命令執行官賣出其債權的賣出命令或選任管理人管理其債權的命令(該法第161條第1款)。惟無論如何,均既可實現對債權人的充分保護,又不致損害債務人與第三人的利益。
四、我國法上的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及其檢討
(一)我國法上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規范體系
在《合同法》頒布之前,我國沒有代位權制度的規范基礎。1999年通過的《合同法》則在第73條對代位權制度作了明確規定。依該條:“因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的債權,但該債權專屬于債務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權的行使范圍以債權人的債權為限。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必要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1999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雖然在我國《立法法》頒布后,司法解釋作為法源的合法性受到挑戰,(注:《立法法》第42條第1款規定:“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因而,最高法院應沒有法律解釋權。)但至少由于司法實踐的慣性作用,司法解釋對于各級法院的審判工作仍將產生可以預見的實質性影響,因而對這部分規范的研究仍然是有意義的。《解釋》第11條到第22條是對代位權的規定,其中第13條和第20條分別是對代位權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具體化,最稱重要。依第13條:“合同法第73條規定的‘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債權,對債權人造成損害的’,是指債務人不履行其對債權人的到期債務,又不以訴訟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債務人主張其享有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到期債權,致使債權人的到期債權未能實現。”第20條則規定:“債權人向次債務人提起的代位權訴訟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的,由次債務人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予消滅。”亦即債權人行使代位權后,可以直接用以滿足自己債權。
(二)與傳統民法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比較
應該說,《合同法》就代位權的規定比較中性,而且有很大的自由解釋空間,除細微差別外,我們尚看不出其與傳統民法代位權制度有何本質不同。但是到了《解釋》,不知是出于對傳統民法代位權制度所存缺陷的深刻體認,還是純屬偶然的無心插柳,已經開始嘗試著對代位權制度賦予新的含義。其與傳統民法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在立法體例上:傳統民法除法國法將代位權制度規定于“契約或合意之債的一般規定”(第三章)之“契約對于第三人的效果”(第六目)(注:這可能與法國法體系化、抽象化程度還不太高有關。法國法尚未抽象出如“法律行為”、“債”等概念,雖出現了“債的效果”、“債的種類”等字眼,但其在體例上均在“契約或合意之債的一般規定”之下,因而其與通常“債”的意義并不相同。)外,日本和臺灣地區均將之規定于“債(權)的效力”部分;我國法則將代位權規定于《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
2.在制度價值上:在傳統民法中,代位權的制度價值系為保障全體債權人的利益(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除外);而在我國,依《解釋》,代位權僅須債務人遲延即可構成而不以無資力為要件,行使效果亦可直接滿足債權人債權,因而其是一種通過公權力滿足特定債權的制度,其功能與強制執行相當。
3.在代位權的種類上:在傳統民法中,債權人代位權別為三種,即種類債權之代位權、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與保存行為之代位;在我國,從《合同法》第73條和《解釋》來看,代位權制度均僅適用于請求行為之代位,保存行為之代位并不屬之;而在請求行為之代位中的特定物債權之代位中,其適用的物體為債務人所享有的特定物債權,《解釋》中代位權的物體則僅限于“以金錢給付為內容的到期債權”,金錢債權非屬特定物債權應無疑義,因而特定物債權之代位權在我國亦無存在余地。在現行法制下,代位權僅包括種類債權之代位權。
4.在構成要件上:在
傳統民法中,種類債權之代位權以債務人陷于無資力為要件;而在我國,依《解釋》第13條,則不以此為必要。
5.在行使方式上:在傳統民法中,對代位權的行使方式,一般無特別限制;而在我國,代位權須依訴行使。
6.在效果歸屬上:在傳統民法中,代位權行使的效果歸屬于債務人,代位權人不得徑行滿足自己債權;而在我國,依《解釋》第20條,代位權行使的效果直接歸屬于債權人。
由上述,我國債權人代位權制度與傳統民法已有根本不同。
(三)我國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檢討
應該說,最高法院勇于嘗試的精神,值得欽佩,(注:日本學者平井宜雄最近提出代位債權人就被代位之債權應享有優先受償之利益,該國判例也通過賦予債權人抵銷權而部分地承認了該種優先受償效力(戴世瑛,前引文,第99-100頁),但在立法或司法上對該種效力一般地予以肯認,似乎獨最高法院一家。)而且,該種嘗試確也能夠彌補傳統民法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某些不足,如有學者指出使代位權行使的效果直接歸屬于債權人,即可避免傳統民法債權人行使代位權動力不足的問題。(注:曹守曄,“對合同法中代位權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法院報》,2000.3.3。)但是,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在解決部分問題的同時,其能否融于既有的法律體系,合于既有的法學理論?特別是,既然該種代位權制度與強制執行功能相當,何不直接將之規定于強制執行而另辟蹊徑?
1.債務人的訴訟地位如何安排?
與傳統民法代位權制度相同,我國法上代位權的要件并不要求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已經裁判確定,在代位訴訟中,債權人與債務人對他們之間的關系,如債務是否存在、其上有否抗辯以及損害賠償數額等,可能還存在爭議。因此,我國代位權制度仍難避免傳統民法代位權制度下,代位訴訟中債務人訴訟地位難以安排的尷尬。
(1)債務人能否成為第三人?
就此問題,《解釋》第16條第1款規定:“債權人以次債務人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權訴訟,未將債務人列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債務人為第三人。”那么根據該條,債務人應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還是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與本訴的原被告均處于對立地位,在該第三人提起的訴訟中,本訴中的原、被告應均為被告。而上文已經指出,代位訴訟中,債務人與債權人、第三人均既有利益一致之處,又有利益相反的地方,與之均不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而且,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享有第三人之訴的訴權,其是否起訴,屬于當事人處分自由的范疇,不應由法院或者其他當事人決定,故《解釋》所指第三人應非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那么,債務人能否成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固然可以由法院追加參加訴訟,但是,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必須站在原告或被告一方,而在代位訴訟中,債務人與債權人、次債務人均存在對立的關系,不可能完全站在其中一方,因而債務人也不可能是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
(2)債務人能否成為共同訴訟中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共同訴訟包括必要共同訴訟和普通共同訴訟,后者是指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人民法院認為可以合并審理,并經當事人同意的(《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款后段)訴訟,代位訴訟顯然并不屬之;前者是指“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2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民事訴訟法》第53條第1款前段)訴訟,而共同訴訟人必須對該訴訟標的利害一致。代位訴訟的訴訟標的在我國有兩個:一為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法律關系,一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間的法律關系(《解釋》第20條參照)。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就后者二者利害一致,而就前者則利害對立,因而,無從作為共同原告;在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則利害關系正好相反,因而亦不得作為共同被告。
通過以上論述,債務人參加訴訟的可能性均已被排除,則何以在當事人法律上不能而非主觀上不愿參加訴訟的情況下,其與債權人、次債務人間的法律關系均得經裁判確定并及于該債務人?對債務人的訴訟權利是否缺乏應有的保障?在筆者看來,對債務人的訴訟和對次債務人的訴訟原本就是兩個各自獨立的訴訟,并無合并審理之可能,硬行“拉郎配”試圖簡化程序,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2.債權產生支配權?
在傳統民法理論上,債權是請求權,債權人只能請求債務人清償,對其特定財產并無支配權,除非其上有擔保物權(但這時的支配性是擔保物權的效力使然,仍與債權無關)。但依《解釋》,則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情況下,債權人可以以債務人的債權清償債務(雖然須經法院裁判,但裁判亦須有實體法上的根據,對當事人間原不存在的法律關系,法院應無自由創設之權),這與債權質頗相類似,但債權人根據其債權何以能夠支配債務人的特定財產?似乎并不能找出有說服力的理由。而且,該種做法,對其他債權人是否公平,亦值商榷。
3.強制執行制度之完善
無論是傳統民法還是我國民法中的代位權制度,均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法律關系尚未經裁判確定的情況下,即使債權人對債務人債權享有某種權利,這一方面使債權人過早干預債務人事務,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難以解決甚至無法解決的理論問題。因而,兩種制度應均不可取(保存行為之代位除外)。欲使債權人對債務人債權享有某種權利,我們只能如德國法那樣求諸強制執行制度。在這方面,我國民事訴訟法已有相關規范,(注:相關規定,可參見《民事訴訟法》第221條、第22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0條。)但仍嫌單薄,亟需借鑒德、日及臺灣地區相關規定以期完善。
結論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除非保存行為之代位,無論傳統民法中的債權人代位權制度還是我國民法中的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從構成要件和價值判斷的角度而言,均無存在之必要。取而代之的,應為就債務人對第三人權利的強制執行制度。
不僅如此,以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為個案,對我們的法律移植也許會提供某些啟示:歐陸法制發達國家的法律史,如果從羅馬法算起,已經有數千年之久,其間法律傳統幾乎沒有中斷過,因而,這些國家具有豐厚的法律文化的積淀,法律制度也已日趨完善,我們在“拿來”時,固然應該懷著無比景仰的心情,自覺地承受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盲從,不應該放棄自己獨立的思考和批判的精神,而應在虛心繼受的前提下努力尋求法律的突破,用一句時下流行的話說應“與時俱進”。但是,這種突破又必須慎之又慎,必須是在大膽假設基礎上的小心求證,這樣,我們才可能一方面繼受先進法律,另一方面真正推動法律的演進。其間分寸的拿捏,誠非易事,需要整個學術群體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努力。愿以此與學界同仁共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木右式
【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之檢討】相關文章:
債權人申請書09-08
債權人申請書08-18
債權人破產申請書09-07
債權人破產申請書04-25
論間接占有制度之存廢08-05
完善我國反訴制度之設想08-12
公司設立無效制度之研究08-05